Episode 1 | From Old Beiping to New Beijing, Hometown and Foreign Land, Culture and Identity – Zhang Beihai, Shao Fan, Xu Zhiyuan


“任他弱水三千,我只取这一瓢。为什么只取这一瓢,我只能说写作随缘。”旅居纽约的张北海老先生回到北京,霜降之夜在玉河边的天安时间当代艺术中心与朋友们秉烛夜话。这是天安时间当代艺术中心新空间暨「Jensen’s Garden」艺术展开幕后,又一个思想与激情碰撞的夜晚。艺术家叶永青、邵帆、作家许知远以及其他五十位艺文界人士济济一堂,在玉河一号的院落深处,竹林掩映中,美酒炉火相伴,漫话故土与他乡,文化与身份,传统以及我们置身其中在创造的当下生活。

玉河夜话现场
从北京到台湾,从台湾到纽约,1936年出生的张北海十二岁离开故土,先后经历了两个时代,三种文化,和他心中的“八千里路云和月”。老先生几十年来一直埋头围绕纽约、北京两个城市写作,他的小说《侠隐》,圆了他一个老北平的梦,他一再说过自己“只愿侠梦不要醒”;走到今天,他又收拾好自己在纽约多年的心事,奉上《一瓢纽约》。而鲜有在公众场合讲话的他,这次循着他的梦彻底敞开了话匣子。从中文到英文,从大陆到纽约;从满清时代的老胡同,到纽约的第五大道。他怀念雍和宫,怀念他儿时的嬉戏打闹处北海公园。当1974年第一次回到阔别多年的北京,他从华侨大厦顺着模糊的记忆找到位于东四十条的老家,忽然不知自己身在何处。他在那里出生,那个院落却不在是自己熟悉的样子。

作家张北海
回忆旧世界,令张北海感到恍惚。而当下的新世界,糅杂着记忆,也在张北海的眼前不断铺陈、更新、裂变。他的经历引发了当晚许多嘉宾的回忆与思考。艺术家邵帆是个老北京,在他心中北京是个冷冽的城市,而《侠隐》中关于做棉袄的描述勾起他儿时对于“温暖”的记忆。同样作为艺术家的叶永青的“北京经验”则完全不同。他80年代来到北京,从此看着北京疯狂裂变,比起老北京人那种对儿时北京的沉实记忆,他反而迅速积累了对北京的多层参照。叶永青觉得“记忆是比现实更有意思的参照”,就像张北海在纽约写《侠隐》,精神穿越回老北平,瞬间忘了自己身在何处。叶永青认为“远离有时候会产生更真实的观照。”

艺术家邵帆

艺术家叶永青
作家许知远有着与叶永青相似的感触,认为距离或者说文化的边缘状态反而激发无穷的创造力:“我对‘文化边缘’感兴趣,因为‘中心’经常变得停滞、迟钝,但是边缘会有意外的生命力,使人重新思考生命,重新思考各种文化。如果回顾整个20世纪艺术史,乔伊斯从瑞士跑到爱尔兰,海明威到巴黎重新描绘美国生活,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而与创造力相伴的,必然也有逃离的代价和它给个体生命所带来的无垠的焦虑。在张北海的《一瓢纽约》中,他曾多次述说自己喝威士忌的故事。在许知远看来,与其说那是畅饮,不如说那是对置身他乡的个体孤独感的克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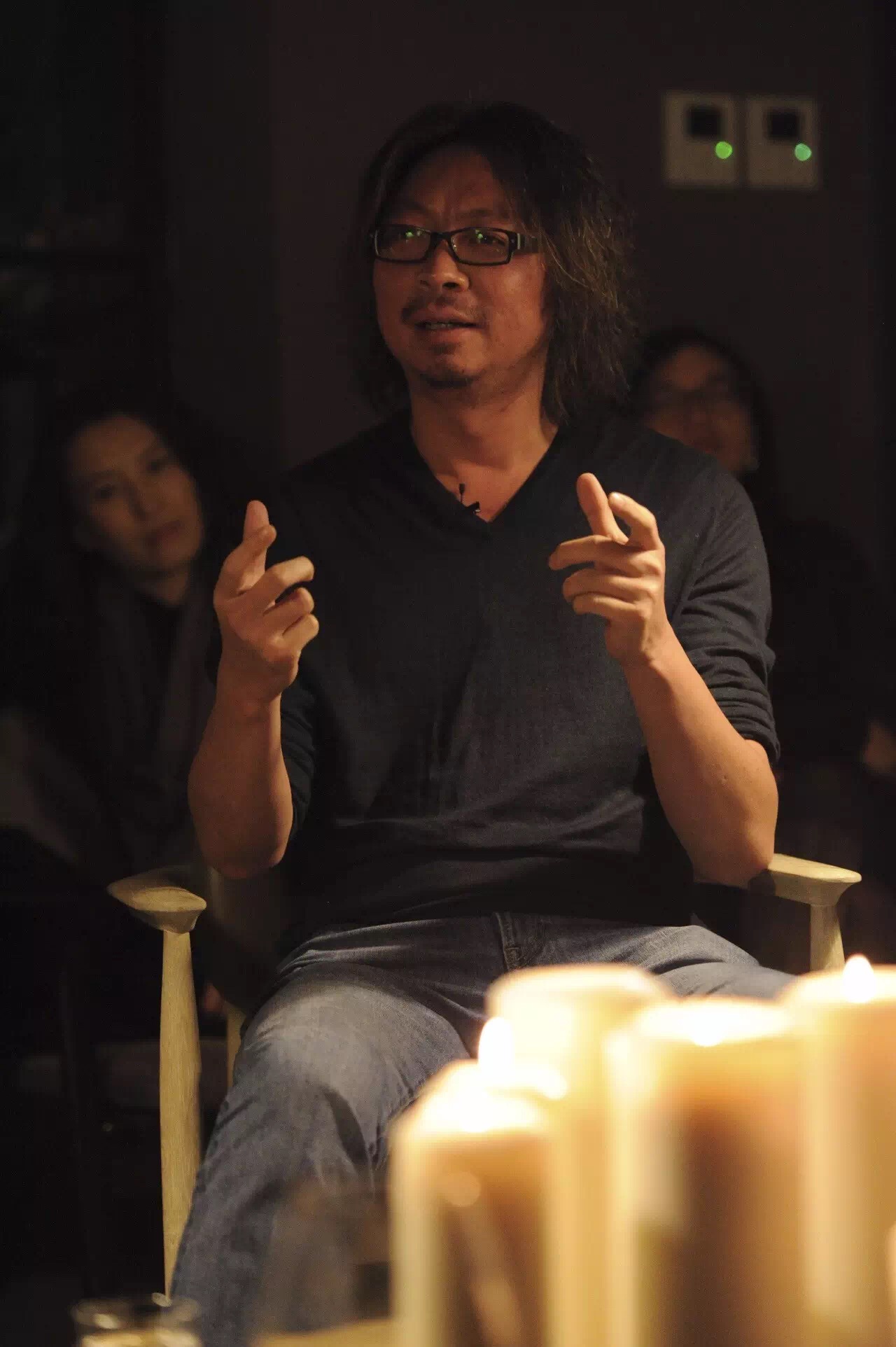
作家许知远
艺术家徐累举例说:“村上春树小说里没有‘父亲’,是没有根的,所以他的作品很容易流动和被传播。回到中国来说,中国情感和文化背景下如何兼顾到两头都能有,未来应该怎么做?”徐累作为许多年轻艺术的导师,还说到现在的年轻人,有一类特别全球化,另外一类则回返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去吸取营养,喜欢《侠隐》中那个老北京。这个问题蕴含着矛盾性,也激发了很多相互观照的创造力。 而十二岁就远离故土的张北海戏称“一直不知道自己应该活在哪里”,所以反而早已习惯性地“摆平”了自己的身份问题,在从小就跳出故土文化的游历中,凭着自己的个性,渐渐有了置身事外的洒脱。

艺术家徐累
然而张北海面临的不光是地理上的大洋两岸,更是两个时代的代际变迁。从年龄上说,他是在场许多嘉宾的父辈,今天他所回到的北京,也已经是一个时间意义上的“新北京”。 时间带来了改变,然而更多是经验上的参照。例如出生于七十年代的《艺术新闻中文版》的主编叶滢谈到,她这一代人的精神历程其实与张北海先生的有一个类似的经验。这一代人青春期刚刚开始的中国80年代是人们大家西方现代主义的时候,人们谈萨特,贝克特,谈艺术也是西方现代艺术。随着90年代进一步的开放,人们有了更多的阅读和游历的机会,渐渐形成“普世的世界主义”。而面临如今加速积累、裂变中的新北京,人们依然有身份的焦虑。这种焦虑从横向来说来源于对不同文化的认知,从纵向来说也来源于历史。用许知远的话说,这样的裂变带来的焦虑就像人们是在某种“废墟上的狂欢”。

左起:主持人陈晓楠、艺术新闻中文版主编叶滢、三联生活周刊主笔曾焱
对于这个问题,张北海愿意从更乐观的角度去看待。他感慨说:“如果这个新北京有灵魂,上街就可以看到。” 年轻人对他的触动最大,那些有活力的、富有冒险精神的年轻人另他感受到代际的迅速:“我不敢讲自己有没有混出来,但我可以肯定地说,如果这个社会缺少富有激情的人,这个社会是没有希望的。不管是在艺术、文学、电影行业,还是在各行各业,少了这样的年轻人社会没有未来的。”
出生于60年代的艺术家邵帆对于年轻人带来的城市活力非常认同,这也是为什么北京会聚集文化和艺术的原因:“北京之所以有活力,除了它自身的底蕴所迸发的,还有很重要的就是外来文化对北京的塑造。所以北京一直特别有包容性,永远有外来新鲜的血液、新鲜文化来刺激它。北京近800年是很辉煌的,过去所谓的原住民也是外来的,他们到一定的时候都开始衰败了,北京永远有新血液的刺激。我觉得像我们这一代老北京是特别傻的一波人,特别傻(笑)。是特别没有竞争力,对任何事情都相对觉得无所谓的一代。其实都是需要从全国各地或者全世界来的人,给北京带来新的活力和张力。”
外来文化的确给不同代际的人带来的非常不同的影响,也注定了不同代际的人在文化和身份认同方面的感触完全不同。70年代出生的许知远认为他这一代人可能是最后一代对西方文化有强烈焦虑感的一代,更能年轻的一代焦虑感明显消失了:“我觉得这10年有很奇怪的变化,过去所有资源特别难以获得,现在获整个互联网带来的区域中心化,使年轻人对于中心的渴望明显弱化了,这一代年轻人对于历史扮演角色不感兴趣了,一方面带来自在和自由,而另外一方面我也感觉到他和那个传统或者更大的世界产生紧张感消失了,带来创造力的萎缩。”
在生于不同年代的嘉宾的讨论中,张北海陷入了对老北平更复杂的回忆。他讲述的那个老北平有时候很极端,有时候又很诗意。说道这几年回北京的体验,他说:“现在的纽约不再是E.B怀特笔下的那个纽约,北京也不再是我梦中的老北平了。北京灵魂已经消失了,今天新北京是什么?我有时真的无从说起。”张北海承认这是世界上每一个大城市所必然经历的发展中的阵痛。历史上的巴黎、伦敦、纽约无一例外。 而我们的新北京,依然处在裂变的过程中。“高楼大厦越多,人的灵魂才变得越重要。如果人没有精神的话灵魂就没有了,那么这样的地方不能够称之为城市。”

作家张北海
艺术家邵帆则一直关注这个城市的美学,认为审美在某种程度上比文化还重要。北京的美感,在他看来是这个城市层层叠加的厚度:“北京的厚度有一种叠加。到清朝的时候北京城一直到民国,再到北海先生笔下的30年代的北京,再到我小时候70年代的北京,还有80年代,还有现在的裂变时代,真的是好多层的叠加,特别有意思,这么多层才有了北京的现在的厚度。”


玉河夜话现场
在天安时间当代艺术中心创始人翁菱看来,这次相聚让我们对老北平和新北京又有了新的认识,来自于不同时空和领域的声音激发了全新的思考。在社会疯狂变迁、城市迅速裂变的今天,作为个人应该如何在这个世界自处,以及应该如何将自身的经验分享和传承?而“玉河夜话“这样轻松而又深入的对话是接下来北京天安时间当代艺术中心一系列“艺文中国沙龙”的序曲,天安时间希望通过这样的沙龙相聚,为社会带来更多具有启示性的话题。将来天安时间和Georg Jensen将一起举办不同方式的聚会,让人们拥有一方安静之地,一个隐藏在老城中心的精神家园。

作家张北海与天安时间当代艺术中心总监翁菱


玉河夜话嘉宾与友人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