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isode 17 | The Energy of Art II – Art is the Highest Form of Hope – Hans Ulrich Obrist, Liu Jiakun, Ma Yansong, Wang Jianwei

导言:当今世界瞬息万变,充满颠覆与重塑。在上次「玉河夜话-艺术能量」的探讨中,崔健与沈伟以艺术家的真挚和创造力震撼了我们。本次「玉河夜话-艺术能量II」,我们围绕艺术与其他领域的跨界合作以及这样的合作所能产生的社会能量进行了深入的讨论。Hans-UlrichObrist提到,在全球化的大环境造成了各式各样的灭绝——语言的灭绝、艺术类型的灭绝甚至文化类型的灭绝。这个过程必然也伴随着个性的丧失。我们如何在这样的全球同质化过程中寻求到新生,或许可以在超越单一领域的合作中找到全新的答案。这是一条需要持续探索的道路,它未必以最直接的方式带来改变,但却是最高形式的希望。
以下为现场精彩对话节选:
艺术能量——从艺术家个体的创造力到跨领域合作
翁菱:今天的“玉河夜话”是今年夏天的第一期。 “玉河夜话”是在北京胡同中心一个非常难得的好朋友相聚、跨界思想讨论的聚合平台。今天是“玉河夜话”第二次讨论“艺术能量”这个主题。2016年11月冬天沈伟和崔健两位艺术家朋友进行过一次关于“艺术能量”的对话。他们从自己的创作为出发点,以自己的创作可能抵达的高度和影响力来讨论他们对艺术的思考和实践。本期我们想从宏观的跨界合作的角度去谈“艺术能量”。
今天的四位嘉宾分别是伦敦蛇形美术馆的的Hans-Ulrich Obrist、著名建筑师刘家琨先生、马岩松先生,以及观念艺术家汪建伟先生。

“艺术在你没有想象到的时候与你相遇”
Hans-Ulrich Obrist:非常感谢翁菱的邀请。确实我认为我们总是应该去超越我们知识的边界,将各种学科融合在一起。所以我感到“玉河夜话”是一个非常好的形式,能够让大家进行开放而专业的交流。在21世纪我觉得我们需要去解决的是我们这个时代非常重要的一些议题,这样我们才能真正产生一种联接。
当我收到关于“艺术能量”的主题的邀请的时候,我看到两位著名的建筑师出现在我们的嘉宾名单中,我们是不是能把这个论坛叫做“艺术能量”或者说是“建筑能量”,因为我觉得两位建筑师都有能量实现这个转型。
我这里想首先给大家分享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实际上是在去年夏天发生的,当时我刚去美国回来,差不多早上6点抵达伦敦。 在出租车上,出租车司机说想给我讲一个故事,我表示愿意倾听。他就把发动机关掉讲去年夏天发生的故事。他当时是和爸爸一起去了一个博物馆,之后在肯辛顿公园,遇到了我们的夏日凉亭。因为凉亭在公园中心位置,所以它们并没有门,是完全开放式的,免票的。他说当时带着一只狗,狗直接冲进凉亭。他去找那只狗,却突然发觉以前从来没有去过一个博物馆。我问他为什么不去看展览,他说他相信展览不是面对他这样人群的。我觉得他分享的故事非常有意思,对我有一些启发。他说自从那天开始,他就开始带着小女儿逛博物馆,他小女儿也开始去读一些关于建筑方面的书,后来他女儿真的成为了一名建筑师。
我之所以给大家讲这么一个故事,是因为我坚信这么一个想法,我们需要看到这种转型,特别是在思想当中转型。特别是这种转型在什么时候最强烈,你根本没有想到的时候可能是非常强烈的。就好像有一本书里面有一句话非常好:“艺术在你没有想象到的时候才会和你相遇”。我坚信这一点。我们希望能够创造的不仅是免费给普通人接触艺术的机会,并且是创造公众艺术或公众建筑的机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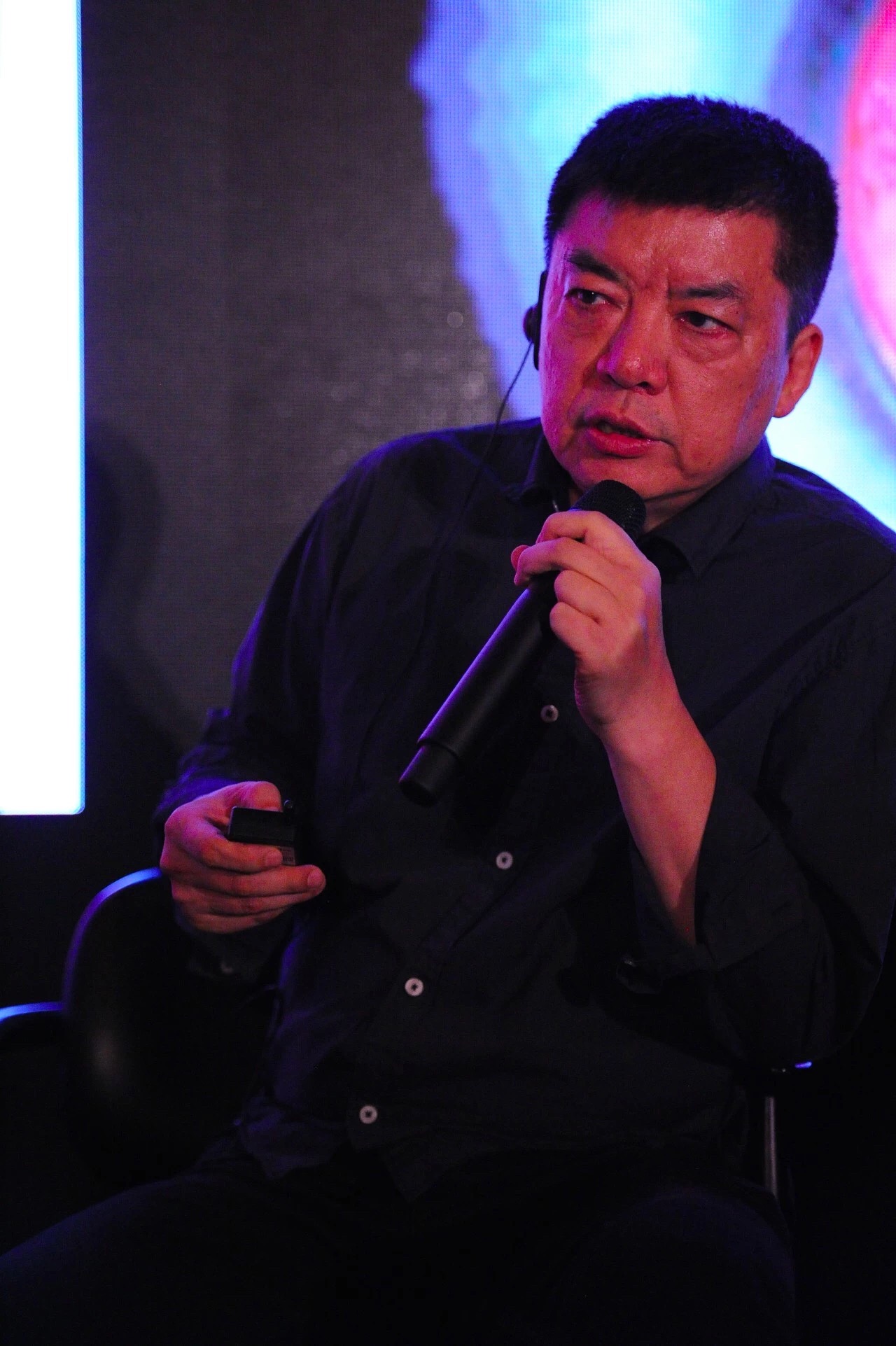
北京“夏日凉亭” – 超越表象符号,表达内在的东方意识
刘家琨:我的工作就是盖房子。首先我介绍一下之前的工作。这是我成立事务所之初的成名作鹿野苑博物馆。这个博物馆主要是强调建筑和自然共生我。我把林间空地和竹林,一个光明的大厅,一个绿色大厅,然后建筑拆开和自然的东西混在一块,把它们平等的对待。它包括自然包括很多元素,用植物、水、天、光一起最终来体现这个展品主要的诉求,也就是安详以及万物同在。

鹿野苑石刻艺术博物馆(摄影:家琨建筑)
接下来是一个地震后的小项目。我为一个地震当中死去的女孩做了一个也许是全世界最小的纪念馆,只有账篷那么大。这个项目我的体会就是作为一个职业设计师怎么去掉自己所有的技术方面的诉求达到无我状态。就是以对象的需求为目标,排除掉一切设计的手段,朴素到底,因为这是一个为普通的小女孩做的纪念馆。最后我想“无我”是在调动其他的力量。

胡慧姍纪念馆 (摄影:家琨建筑)
接下来是一个关于酒的博物馆。地震以后我用废墟材料做了重新打碎做的再生砖,在城市里建成的第一个公共建筑。当然除了再生砖这样一个环保材料,主要是再生砖里混杂的东西和酿酒所需要的一切混合的微生物,各式各样材料混在一起的那种感觉,那种土性。所以业主接受这个项目是出自于一种直觉就是感受到万物混杂在一起的土性。

水井街酒坊遗址博物馆(摄影:家琨建筑)
另外一个再生砖做的项目,是瑞士诺华的办公楼。除了再生砖还有竹子这样的材料,其实主题是不用任何一种传统符号,而是通过光线、阴暗、曲折路线传达出东方文化内在的逸韵。

诺华上海园区c6楼(摄影:存在建筑摄影)
接下来这个项目是“西村大院”。 西村大院是特别大的一个院子,就是我沿着周边修建形成一个巨大盆地,其实有一点像四川的火锅,把所有的动作和人的行为都装在里面。这个项目特别大,自行车和跑步都可以跑到房顶上。这个有一点像矩形结构,大的是里面装载了可能发生的没有被商业规划的过去一些行为,一些休闲的行为。

西村大院(摄影:存在建筑摄影)
接下来是刚刚完成的苏州金砖博物馆。金砖就是给故宫铺地的大地砖,这个项目主要是表达从一个地方性物质原料到一个王朝最高殿堂的精神历程。这个项目既不是砖窑也不是宫殿,而是有宫殿感的砖窑。整体展览非常简单就是用了方块,但是用了很多砖成了一个砖的编年史。

御窑金砖博物馆(摄影:存在建筑摄影)
然后就是这次蛇形美术馆北京夏日凉亭。我用了一个弓箭原理,因为地点在王府井,又是蛇形画廊在运作,那么在这样一个历史深厚地方又有国际化前沿运作团队我需要找到一个点。我想超越在国际上都用了很多年的中国的表象符号而来表达一个更内在的东方意识。那么弓箭就是这样的,弓箭拉开以后是充满能量但是隐而不发的姿态,其实是比较典型的东方意识。
这是我的草图,根据弓的原理做的这么一个结构。因为蛇形美术馆有一个很重要主题是挑战建筑学的实践极限,挑战建筑学的边界,我想同时除了我刚才说的要表达的那些东西,我还想创造一个新的结构。这个主题是关于“力”。力是放之四海无处不在的,但是怎么样对待“力”,这其实不光是技术的态度,其实也是一种文明的态度。我是想通过怎么样对待“力”来表达一种东方特有的态度。
这是立起来,把很多钢板跌在一起立起来,通过钢索强力拉弯就像开弓一样,这是钢板一层一层组合,越往高越少,这个原理可以叠加,弄得特别高再拉下来。这是一个受力状态,因为建筑学概念当中一个东西需要形成会很厚,但是我们其实只是用了5层弹簧钢板,有一点像汽车弹簧特别薄但是会形成拱的结构。
它是可以变的,因为动图可以看到每一个都有弹性的,不是像现代建筑和自然和重力硬抗的感觉,其实可以随机变化的,这个变化就带来了很多形态可以全视频,可以是拱,可以反翘,拱像阿拉伯的,那个反翘像中国传统建筑。
这个凉亭是我在威尼斯双年展上的一个作品延伸,不是拍脑袋想出来的。那个作品当年主题是“全世界的未来”。我想表达,就是我在后面用很多圆木压住一排钓鱼杆,后面几百公斤,后面只能承受一个矿泉水重量,这是一个极限平衡。我想用牵一发动全身的危险平衡来呼吁当年主题,这就是当年的状态。后面是圆木压着,另一面是一个悬着的箭,根据威尼斯太阳的变化其实在每一个时段在上下动作。悬箭就是典故里那个意思,就是表达危险的平衡,这上面有磁铁,很多人在那里留言。
那是不稳定装置性重力悬垂状态,这一次蛇形美术馆做了建筑方面的尝试,我想转化成一种稳定的结构,所以根据弓箭的原理做了这个凉亭。其实当拉索把它拉下来以后就形成了非常稳定的内在平衡的,就是充满能量,内在非常紧张,但是又各方面自我平衡的那样一种状态,形成了真正的结构。我是一个建筑师,创造新的结构其实是我的梦想。
这一次因为靠近故宫,我就用了两边飞翘起来的状态,向传统大屋顶的致敬。当然到阿拉伯可以两边垂下来,这是有弹性的,这是关于“力”的态度,不是硬抗而是顺应、利用,因势利导。
后面有一个你看得见有钢索,其实松开或者紧钢索这个东西是动的,可移动,如果不怕麻烦的话随时都可以动。


(摄影:王府中环)

(摄影:王府中环)

(摄影:夏至)
艺术、资本和科技结合的时代,艺术的未来在哪里?
马岩松:今天讲艺术可以改变社会,艺术能够对社会有影响,我对这个其实不是特别了解,因为我觉得我去博物馆、去看艺术作品的兴趣越来越少。建筑我比较了解,我觉得建筑跟上一代,也就是说差不多20-30年前建筑界相比现在变得非常的实际、非常的合作。
我是指建筑非常合作于资本和权力。因为建筑本身有这个性质,没有资本和权力建不出来一个东西的。所以建筑师很自然的可以说把一个正确的东西变成他成功的一个因素。比如说一个开放的空间,所有人都能来的空间,我觉得刚才说到“免票”这件事,我觉得所有人能来的空间不一定是一个好空间。
有时候我讲到新的希望小学,一个希望小学不一定是一个好学校,至少对小孩来说其实一个所谓的私立学校和一个希望小学对他们来说是完全一样的。但是现在我们评论建筑的时候就会觉得作为一个希望小学首先是一个正确的东西,把它跟一个好建筑混淆,就是这样的混淆非常非常多。因为政治上正确的东西也变得非常非常多,错误的东西大家不敢说了。如果跟前一代那些像刚才说的扎哈这一代人相比,以非常个人的反主流的力量来定义建筑,当然很多人批评他们“说你这个建筑太个人了,为什么是你的”,现在特别批判这个东西。
我觉得最后一个就是央视在北京的大楼。一着火大家都很高兴,有一半是因为不喜欢央视,有一半是不喜欢这个建筑。可能这样有他个人的有批判性的建筑就基本上灭绝了,就是在那一代以后就灭绝了。我有时候就想更年轻的一代建筑师,全世界的建筑师,现在稍微有影响力的都是在政治上比较正确的,然后作品我觉得跟上一代建筑师简直没有办法比,完全是靠有话语权的人去支持他们来定义他们的价值。他们完全没有多少作品能够反叛,说能改变这个东西,这是至少我对现代建筑的一种理解吧。
而且我发现在文化界和艺术界对建筑的期待,也是最好应该是一个很正面积极的。如果他们出现批判性,大家会质疑你为什么花这么多社会资源、钱和力量去实现一个所谓的批判性。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到现在还有很多人会去质疑上一代的人。1988年MOMA有一个解构主义8人展,他们当时是大概40岁左右,后来被我们现在称为大师,现在已经不太干活了。但是当时我觉得他们40多岁的时候对世界的挑战是非常大的,如果没有这个挑战,那么后来的30年,我觉得公众对建筑会完全是无视的。因为他们的存在大家才会关注建筑。如果说我们这个行业没有改造世界的热情和野心的话,公众也会对建筑问题丧失兴趣,如果这样的话很难谈到某一个专业对世界有改造的可能性。

翁菱:刘家琨刚才讲自己公共建筑时候给我们解释他所有建筑的素材、功用和背后的用意、意义和隐喻,这好像跟艺术圈有一点相反的感觉。马岩松其实在表达艺术、资本和科技结合的时代,艺术的吸引力好像越来越弱,做建筑也越来越艰难,真正理想主义的建筑可能是越来越难实现。那么,汪建伟怎么看艺术和建筑跨界创作的这样一个时代呢?
汪建伟: 其实我今天突然想讲一个非常新的概念,这个新的概念产生于40年前的一句话,这句话叫“摸着石头过河”。这句话至今在影响着我,所以说我认为它是新的。因为这句话在40年前我们第一次听的时候我们只是从第一个时间理解了这句话的意思,是因为我们前面没有路可走,没有任何路可走,所以我们必须摸着石头过去。
过了20年我重新理解这句话的意思,为什么叫摸着石头过河,就是说如果你不行动的话你一定会淹死的,但是如果你想不淹死你必须过河,但是后面有一个潜在危险,如果你过河不一定意味着你还会活,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一句话。
然后在今天也就是说前几年,当所有话题都集中在今天的科技,集中在今天我们对这个世界的不理解,碎片、智能、科技改变我们所有生活和命运的时候,我们开始突然想起我们的传统,突然我发觉这句话第三个意思在今天非常有意思。这句话意思是既然是摸着石头过河,是必须要过去的,你没有退路可走,所以说我理解这句话第三个意思是今天最新的解释就是“不走是死,走不见得你会活着。”实际上我理解从这个意义上来讲艺术和建筑都是一样的。

Hans-Ulrich Obrist:去年我们也很关注人工智能这么一个话题,因为我感觉到这个话题对我们来讲非常相关,我们想谈一下到底艺术和人工智能之间有哪些结合点。不光是解决问题本身,我们同时希望做一个展览,然后在博物馆里面,我们有一些人工智能的人物。 这种人工智能的信念在蛇形画廊里运用在给我们一些访客做指导。人工智能有自己的特征、有自己生命的感觉。这对于访客来说是全新的体验,许多访客在留言本上讲到这种体验非常不一样,他们以前没有感受到这种差异,没有体验过这种体验,所以这是全新的体验。这给我们带来很多在艺术当中的问题,就是你要思考,包括讲到“艺术能量”这样非常大的问题的时候,到底人工智能时代里艺术能量是不是容易发生变化?而且我们可以想象在机器和人类精神之间这种互动,如果我们不了解到底什么是意识,那么我们如何来进行智能的量化。
还有我们现在是不是去定义机器的道德太晚了,当然这是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不能忽视。当然很重要的就是这种未来是不是属于非人类实体,是不是对我们的现实形成了一些威胁。我们希望通过这种讨论和我们的艺术展览来进行这种话题的探索,我们所作的这个展览,包括今年的活动当中我们都想要去探讨艺术是否会在AI的时代所消失,是否会受到人工智能的威胁。那么今年我们的话题可能就是艺术和人工智能,也可能会想到一个更好的话题或者更好的意义题目,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探讨。
“艺术是最高层面的希望”
Hans-Ulrich Obrist:我记得我第一次见到汪建伟的时候是在97年的北京,当时我们是做一个展览研究是叫做“移动中的城市”。当时我们一直说汪建伟就像甲骨文一样。我在这里想多说一句,因为可能比较有意思,就是我们总是说这些艺术能量的概念或者建筑能量概念过去是一个非常大的事件,某种程度上我们如何细分,然后变成实际的想法。我们总是谈大环境变化,我觉得艺术是最高层面的希望。如果把艺术看作是一种希望的话,在这种灭绝的大环境变化当中,那么当然我们必须要去看全球化到底给我们带来什么影响,全球化当中到底多少力量影响。
我们知道这个过程当中可能会出现语言消失、书法的消失、手写的消失。我每天都要发很多的信息一直抵抗手写的消失,某种程度上很多东西在慢慢灭绝。不光是物种的灭绝,同时还是一种类型的艺术灭绝,很多文化现象灭绝等等。所以说我们要抵抗各式各样的灭绝,那种全球化所造成的同质性的灭绝。
解决方案就是全球性对话,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用拥抱可能性。我们将去拥抱潜在可能性。我们需要来超越单一的领域,然后防止丧失我们自己的特征,它叫做一种“拥抱”。我觉得对艺术、建筑的研究,是关于我们如何改变世界,然后贡献到这种抵抗灭绝的过程当中,关于我们如何去抗拒在全球化或者说隔离主义对我们的影响。
汪建伟:艺术也好、建筑也好,如果我们学艺术史,我觉得技术总是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特质,无论它是传统的、当代的,油画的、装置的还是雕塑的。第一个特征就是我们发明了一个技术,在最古老时候一个人拿着石头在岩石上画下了第一个痕迹。还有一个人也许捡了一个树枝在沙滩上画下他想表达的东西,就是这一个树枝和这一个石头就是一个技术,这个技术把人从自己内心带出自己的内心,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一步。第二步,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分享给所有有同感的人类。
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这种知识产生于器官,同时他能够被所有有身体的人分享。我觉得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像Hans-Ulrich Obrist说灭绝,灭绝其实不是今天所发生的事情,19世纪工业文明让我们灭绝了我们创造某一个东西的能力,就是说所有的工人他们被机器所统治最后他们丧失了自己手工去做一个事情的技能,也就是说他们只能成为无产阶级。然后20世纪是媒体和营销彻底控制了我们的消费。其实我们每天在消费我们的生活,我们是按照媒体给我们的指示在做,它让我们成为我们自己对自己身体消费的无产阶级。
马岩松:我觉得被技术的进步限制和被技术操纵是两回事。因为我发现反正在建筑有一种是时代在变化,技术在变化,什么都在变化,艺术在变化,文化在变化。技术做结果产生了,这样建筑作品无论有没有这个人都会产生,这属于一个时代的结果。就是历史反正就是会怎么发生,还有一种就是比如说我们都知道高迪这种人,你看他也不能说是属于西班牙建筑,但是如果没有奥高迪,西班牙建筑又自成一体,那是顺应时代的建筑史从古典到现在那是一个大趋势。可是有这些人非常个人化的这些人出现,包括弗兰克盖里这些人,很难影响这个时代,结束了就结束了,结束了以后世界还是这样。从90年代初到现在,我觉得现代主义这个大思潮大潮流没有停。
刚才说中国有自己的,我觉得还没有。我觉得中国现在是被西方现代主义完全统治了,至少建筑界是这样。我觉得很难说产生什么新的不同现代主义的思想,这个是影响这么长之时间,中间形成了有不同人产生和结束这个不同。
所以可能作为这些人的价值并不是改变这个时代,而是他们个人的跟时代的不同,就是他们自己也认为,可能没有觉得认为改变这个时代是一个目标。如果你要改变要了解他,要跟他对话你想各种手段的时候,你可能就没有那么自我了,所以我觉得他们可能产生和结束就是最好的价值。也是大家能认为建筑还是建筑,还是有他的魅力的原因。如果只是一个无名的,所有都无名,去顺应历史的潮流,作为人情感的东西和个人东西都不存在的话那就是一个结果了,就是这个专业是没有自己的话语,没有自己的思想,就是一个时代的结果。

大时代的必然:艺术是摸着石头前进、超越
翁菱:马岩松你在做的乔治卢卡斯博物馆,星球大战博物馆,你觉得这是你成为现代主义建筑师当中一个的作品之一?还是说你觉得你在更复杂环境当中成长起来的,到美国去竞争成功,这么一个重要的项目,觉得你会做到另外一个成绩?还是说只是他们的其中之一?
马岩松:我觉得因为我还年轻,没有套路。因为这是一个竞赛,别人都挺大师级的,然后可能自己给自己有一个限制,然后我们就觉得可能会输,就比较随性。
乔治卢卡斯这个人也是挺怪的,他说选择你们呢,他没有邀请任何美国建筑师。后来弗兰克盖里有一点不高兴,但是在美国确实大部分建筑师都非常的商业,我觉得就是他们的成功建立在各种合作非常的好。可能我们那个建筑反而是挺自我的,如果在那个环境下是不太合适宜的,他的选择完全是个人的选择。
翁菱:所以不是资本的选择,而是艺术家选择一个青年艺术家。马岩松的建筑语言其实也很玩得很厉害,这些年一直在提倡“山水城市”。
马岩松:我主要是觉得建筑这么多思想上变得都没有在中国发生,中国30-40年现代主义,这个城市变化这么大,但是影响世界的思想有什么?根本就没有。现在我觉得就像汪建伟刚才说的,要不然把自己弄死,要不然就是只走新路,不管怎么样就是这样才行,就是你得搞新的。但我觉得日本的我还挺那个,因为他们很有危机感就是跟西方不一样,要走出自己的路。西方自己其实也想走不同的路,因为有一点走到头了。
刘家琨: 我想退到一个主体性的、简单的状态,然后来谈一下。刚才Hans-Ulrich Obrist谈到艺术在社会里的角色这样一个问题。通常我来判断一个行业在社会里角色的时候,我通常是看他用什么材料。政治是用的国家、民族、个人命运这样一个材料,所以政治很厉害。金融会用到社会发展、流通、个人物质生活的幸福,所以金融很厉害。建筑用一些物质,然后占据已经不多的地皮,然后建造出一个空间,然后影响人们的生活,我觉得还是可以的。
那么艺术、能量这些对我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当然建筑也是艺术的,反正差不多都混在一起还沾点边。但是艺术到底是什么?对我个人、对我一个建筑师来讲到底意味着什么?因为我看见艺术也在,好像跟政治非常有关系,艺术、权力网之类的。艺术跟金融也有关系,因为现在变成巨大杠杆撬动,资本也非常有关系。艺术好像还没有来盖房子,这个我们还好还有口饭吃。
对我来讲艺术到底意味着什么?也许行外人更虔诚。坦白来讲艺术对我来讲就是有“准信仰”。我不敢说是“信仰”,因为“信仰”很复杂。艺术也是一个江湖,但是艺术对我来说可以牵引着我到达心灵深处精神高峰的状态,所以说对我来讲非常非常重要,我觉得艺术不一定在权力、金融、资本、城市物质空间层面上来起作用,艺术对我这个人的内心起作用,我觉得就是巨大的能量。这是我说的真话。
Hans-Ulrich Obrist:我觉得我可以给大家一个我最喜欢的定义,就是我刚才说过的:“艺术是最高形式的希望”。当然大家也举了很多例子关于艺术是如何实现超越。我觉得艺术是一个大门,不光是一种超凡体验,同时可以进行超越的东西。不是一个门,可能应该是一个门户,让我某种程度上实现超越。
翁菱:探索艺术和艺术能量这个事是无穷无尽的,上天入地再入内心这是没有尽头的事。我们“玉河夜话”会再找机会,再请朋友们一起来探讨这个我们永远没有办法真正回答的问题。但是我相信你看艺术家展望、曾力、叶永青、张晓刚、朱小地、雪松,很多艺术家和建筑师朋友都在这里,我想无论是艺术本身也好,跨界协作也好,我们今天讨论的这个主题虽然很大但是其实也很小,艺术是我们相信的事情,我们一起相聚一起协作,一起把它做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