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isode 7 | Roads and Souls – Lu Peng, Zhang Xiaogang, Zhang Yang

「玉河夜话」第七期——道路与灵魂是关于一本艺术家传记与一部电影的分享会。
艺术评论家、策展人吕澎带着他的新著《血缘的历史:1996年之前的张晓刚》,与艺术家张晓刚一起现场分享这部时代记录的背后故事。张扬导演也带来了他的最新力作、首部从西藏当地藏民视角出发制作的真实电影《冈仁波齐》的玉河一号院子特邀露天放映。
有关张晓刚的个人史,成为记录中国当代艺术起步时期历史的入口,通过个案观照历史,回溯最初的道路,也由此引申出关于灵魂话题的更多讨论。电影《冈仁波齐》则真切表现了主人公的朝圣之路。两部作品的主人公用各自的方式坚守着自己的精神信仰。这是一条怎样的来时路?
《血缘的历史:1996年之前的张晓刚》新书发布



《血缘的历史:1996年之前的张晓刚》新书发布会现场
“80年代中期,吕澎从成都到重庆来找我和晓刚。”艺术家叶永青回忆起自己第一次见到吕澎的情景,吕澎那时候是“典型的国家干部形象”:戴着眼镜,穿着灰绿色的衬衣。“一幅书生的样子。他请我和晓刚吃火锅,我记忆最深的动作是吃完之后,吕澎从裤兜里掏出了一张绿色的100元,当时几乎没有人掏得起一个整张的100元人民币,也只有那一张。吕澎那时候就跟我和晓刚‘做生意’,说请你们吃饭,你们要给我找一本几几年第几期的《美术杂志》,当天晚上吕澎是在张晓刚寝室打地铺睡的。从那时候吕澎给我的印象就是,他是特别善于搜集和整合资料,所以他今天写出这样一本书,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血缘的历史》的缘起
在撰写《血缘的历史:1996年之前的张晓刚》这本书之前,吕澎曾经参与过《失忆与记忆:张晓刚书信集》的编辑工作; 两人亦是多年的好友,为何还要重新去考据这位艺术家过往的生活经历,书写这一本介绍艺术家的书?吕澎给出了三个缘由:

艺术评论家、策展人吕澎
谈到第一个原因,首先是吕澎注意到当代艺术的话题越来越多被市场和价格左右,“从90年代后期开始,尤其是03年04年之后,我们涉及到艺术的话题基本都与市场相关。”
“我们生于50年代的人,历经社会变迁,每当面对新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都会深入的去思考为什么有这样的变化?”2006年,张晓刚的作品卖了差不多100万美金,“他(张晓刚)觉得这个世界疯了,为什么自己的艺术会是这么样的结果?”80年代中期,吕澎和张晓刚酒聚时,还曾闲聊说,“有一天我们的艺术能够卖到100万,大家觉得这不可能。那个时候完全不能想象今天的艺术市场,可是今天的结果是什么呢? 大家认为只要稍稍花一些力气,一些钱,整个艺术市场就可以有很多资本,我觉得这是一个极其错误的现象和思维方式。如何让人们真的去认识我们今天的艺术,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艺术,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
吕澎写这本书的第二个原因,要在大历史的框架下,刻画出有血有肉的个人成长历史,“在我以往的写作过程中,基本都是从大的历史出发,写一个时代的整体情况。大的历史还是在做一个结构,就像建筑的框架,但是我们每个人对历史和艺术有自己的看法。我们如何让今天的人去理解艺术,除了我们从艺术史角度去推动,还应该让我们的观众,读者和关心艺术的人去了解每一个具体的艺术家和艺术现象如何发生、发展的?如果我们了解到一个有血有肉的艺术家的成长历史,我们可以更深入的观察到他这几十年的创作历史,是如何走过来的。”
用简单的概念去解读复杂的历史,是吕澎认为值得警惕的倾向。譬如谈到80年代的当代艺术,很多人认为就是简单抄袭西方,但这样武断的观点很容易忽视其中的时代语境,因此吕澎将写作的第三个理由称之为“责任”。“听起来有一点抽象,但是我认为是最根本的。我们如何看历史?用抽象的表述也许远远不够。作为一个艺术史研究者,我觉得可以用一个具体的艺术家的成长和他的艺术历程回溯历史。通过这样的回溯,真正认识我们今天的成果,这是一个责任。80后和90后听到责任普遍不是很在意甚至有些反感,但事实上是这样,如果子弹没有打在你身上其实你在看戏,如果子弹打在你身上使你倒下,或者你亲人死亡的时候,你认为这才是事实,我们看历史就是这样。”
所以在写作过程中,吕澎很强调使用的材料,除了张晓刚最近写的自述,使用所有的资料都是1996年之前。“换句话说,都把资料、问题、事实还原到历史当初,当我们发现历史当初什么样的时候,我们对今天就应该有更好的看法。由于有了这样的出发点就影响到了写作,我原来搜集最近若干年大量关于张晓刚的文章,报道、采访等等,最后决定97年以后的材料都不看、不用。我们就是直接还原到历史当中。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也许会把问题看清楚。”
“这不是在写我,而是在写一个时代”——张晓刚

艺术家张晓刚
在吕澎写完这本书之后,他第一个将书给了张晓刚。在飞机上,张晓刚第一次读这本书。当他看到吕澎写的早年的自己时,触动之下流泪。因为他忽然觉得:“我看的时候没有那么肉麻。这不是在写我,而是在写一个时代,或者在写这个时代和下一个时代是怎么转变的,是通过个人写这个时代的转变。而我刚好处在这两个时代转变的过程当中,我的人生也好,艺术创作也好,我有幸搭上这辆车。”张晓刚说。
“我们这一代在80年代学习艺术,和现代年轻人不一样,没有那么多的画册、图片或影像资料,只有靠读书去想象自己喜欢的艺术是什么样的。吕澎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为了还原这种感受,他把我们当时看的那些书又重新看了一遍。然后从那个时代的氛围,了解一个艺术家在特殊的时代背景下如何思考和创作,这一点让我很感动。”


「玉河夜话」第八期现场
张扬与张晓刚
作为第六代的代表导演,张扬在很早的时候就认识了张晓刚,对这一代具有独立精神的艺术家充满了敬意。在2005年他拍的一部电影《向日葵》里面,就借用了张晓刚当时的《大家庭》系列作品。那时,他的电影在东京放映,刚好张晓刚的展览也在东京开幕,“有一部分观众是看完了电影又去参加了画展,看到张晓刚的作品时,以为《向日葵》就是一部张晓刚的自传电影。”张扬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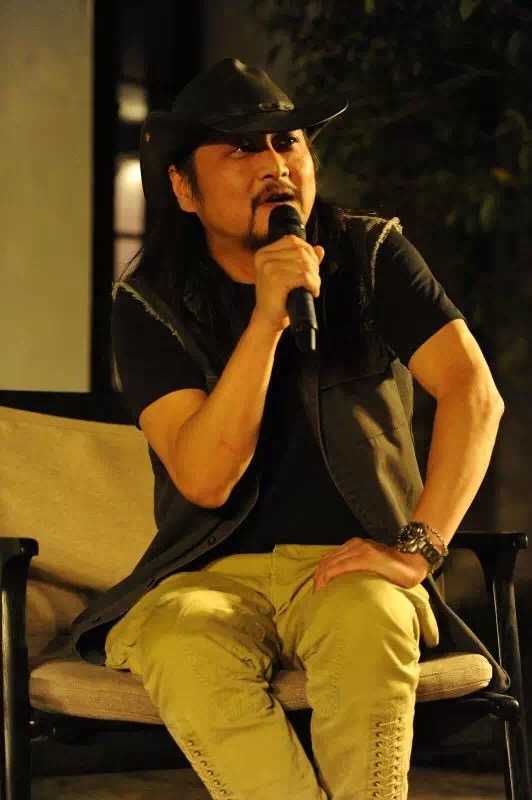
导演张扬
张扬回忆起自己在看了当时张晓刚的《失忆与记忆:张晓刚书信集》之后,感触很大:“我在书里看到东西就是理想主义。其实我们做电影的在今天也需要这种理想主义。我觉得今天的电影领域就像十年前的当代艺术市场,所有的热钱全部扎在了电影这个领域。在这个过程中,我也有过一段时间的迷茫,到底拍什么样的电影,到底怎么去面对今天这样的市场,曾有一两部电影,也想往市场角度去靠一靠。后来那两部电影拍完了,我自己反思一下觉得好象不是我想要表达的东西,自己走了一个弯路。”
《冈仁波齐》


电影《冈仁波齐》剧照

「玉河夜话」第八期现场
早在十多年前,张扬就有了拍西藏朝圣题材电影的想法,这段沉淀的时间给了他勇气。“我觉得还是应该做自己真正喜欢,真正想去做的东西。”整部电影没有剧本,“只有一个想法,和我们了解的一些故事。一群真实的人, 我们跟着朝圣者,一路走一路拍,最终完成的整部电影,形式接近于纪录片的拍法,按照我自己的概念,就是记录式的剧情片吧。”
因为之前去过很多次西藏,看到很多这样的朝圣者,也了解他们的故事。在电影开拍之初,张扬脑中就已经有了一个构想。比如说这11个人的人员构成,完全是我10年前脑子里就已经有的,一个老人,一个孕妇,一个小孩,有一些年轻人,有一家人的,有领舵的……电影中除了老人的死,是我在10年前已经想好的,这一生一死在这一条路上,剩下的都是未知的。99%的故事都是他们在路上发生的。
“某种意义上,既是朝圣者既是在演他们自己,但同时他们又是演员,所以这是很难分别的。我之前拍的电影都是写好剧本找好演员按部就班的拍摄。这一次对我来讲,完全是尝试新的感觉,完全不想这些,只有这一条路,和我想找的这些人。当我找到了以后,剩下的故事是在过程当中一点点看它的发生,看它的发展是怎么样的,然后我们从里边一点点的挑出我需要拍的东西。”张扬说。
不知道拍什么的时候,张扬说你们就磕头吧,每天机器开着就拍朝圣者的磕头,反反复复。这时候一个真实的磕头的人和一个演员的差别就显而易见了。比如说在拉萨布达拉宫拍摄的时候,“我们每个镜头至少要拍三四条,我们拍了一条又拍第二条,又拍第三条,拍到第三条的时候,他们哭了……他们磕头时旁边有转经的人,会催促他们说,‘转经是不能逆时针的,尤其是布达拉宫大昭寺这样的地方。’所以那个瞬间他也会含糊,‘我到底是在拍电影,还是我自己?’其实对我而言,这部电影也是在探究真实与虚构的关系。


露天电影放映会现场
嘉宾朱哲琴谈到她2013年的转山经历时说:“转山是一个很具体的过程,但是当你没有真实的去体验过的时候,转山只停留在人的精神意象里。但当我们今天真正看到了转山电影里的事件,好像离精神的意象又远了很多。就像我当时在路上的时候,其实没有想那么多,可能就是缺氧,每一步都艰难,在想什么时候才能到下一个点。”
而对于张扬而言,他希冀把信仰、精神世界的意象落在日常生活的点滴中。“其实电影从头至尾就是吃喝拉撒睡,在账篷里聊天,说几句话,然后磕头,这是我观察的他们最基本的形态。甚至在村子里边,他们也是每天早上念经,转白塔,然后就是吃喝拉撒,种田,放牧,一天的日子就这样过去了。”
但是信仰本身确实植根于他们身体里,“所以电影中两个小孩,一个是刚出生的孩子,一个大概是10岁的孩子,这两个人物对我来讲非常重要。因为信仰对他们来讲是从出生那一天开始的,可能听到的第一句话就是一句经文。像这个10岁的小孩,我们在路上遇到很多这样的家庭,大人带着刚出生的,10岁、18岁的孩子一路朝圣,这是一种潜移默化的影响。”张扬说。
嘉宾陈数非常欣赏张扬导演的拍摄态度,他认为正是这种客观、平等的心态,让观众真切感受到了朝圣之路和他们的生活。
张扬坦言,这一年的旅行也是一种修行,这个过程是一个发现自我的过程:“我认识挺多活佛,我跟他们是很平等的在一起聊天。可能从我自己来讲,我是六根不净的人,没有想去皈依或者怎样。但在西藏这一年行走和拍摄,就好比今天的活动主题‘道路与灵魂’。对我来说,可能没有一个具像的宗教,但这一年的旅行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一个修行之路。我自己在那里修行,修什么我也不知道,也不能说走完这一趟就找到什么东西了,但是对我来讲这个过程确实非常重要。”
回溯上世纪80年代中国当代艺术开始的探索,到张扬《冈仁波齐》中的朝圣之路,也许这种坚持正是“道路与灵魂”的主旨吧。

导演张扬、天安时间当代艺术中心创始人翁菱、艺术家张晓刚


玉河夜话嘉宾及友人合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