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isode 12 | Existence and Inquiry in the Haze Era – Ma Jun, He Li, Cao Fei, Zhu Xiaodi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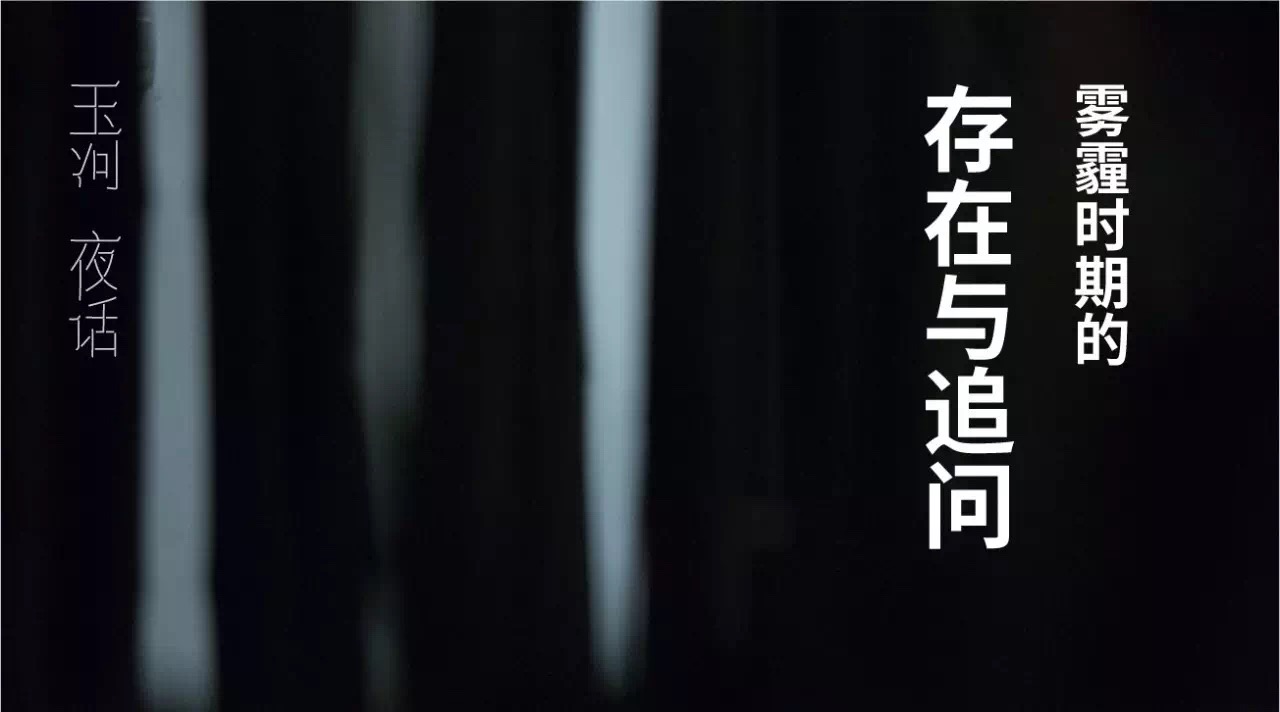
代表天安时间当代艺术中心和Georg Jensen Hus,感谢冒着霾雪来到「玉河夜话」现场的各位,我很感动。其实面对“雾霾”这个沉重的话题,我的内心是恐慌的。多年来关注环保领域的经验,让我习惯了看到问题就找机会去呼吁、去解决,但面对“雾霾”,我好像真的无所适从。今晚的一场对话,我的内心得到了很大的宽慰。这并不是说我忽然找到了解决雾霾问题的答案,而是在各位专家的无私分享中,这些问题清晰地浮现了出来。就像何力主编所说,我们处在“后雾霾时代”,谁也躲不开环境的霾、社会的霾、人心的霾。这一点,对我们所有的人来说都是平等的,无法回避的。虽然越是深入这个复杂的话题越让人感觉孤独和悲伤,但正是因为如此,我们才有了触底反弹的力量。那么接下来,假以时日我们或许能够将这些问题慢慢解决。“螳臂当车”,一场「玉河夜话」改变不了什么,但希望它点起的火苗能借着风声燃得更久一些。
——翁菱
2017年入冬以来,雾霾侵袭了多半个中国。1月16日,玉河霾雪,我们围炉夜话、相聚谈论与雾霾相关的话题。这一次我们荣幸地邀请到了公众与环境研究中心主任及《蔚蓝地图》创始人马军、资深媒体人及《界面》主编何力、北京建筑设计研究院院长及总建筑师朱小地、以及著名当代艺术家曹斐,在四位不同领域专家的引导下,深入地走进雾霾时代的核心问题 ……

朱小地、马军、曹斐、何力(左至右)

“后雾霾时代”的思考
何力:这几天我还是有一点担心的,因为看到最近天气这么好缺乏一个谈雾霾的情景,没想到「玉河夜话」气场强大,要什么来什么,今天我们终于“喜迎雾霾”啦!当然这是一个玩笑!我原来一直在做财经类新闻,好像任何事情都需表现出某种姿态,实则什么事情都没有深究,一辈子也就这样混过来了,所以感谢「玉河夜话」和翁菱给我这样的老同志提供出场机会,让我们一起来谈谈切实的问题。
今天在座的几位朋友都是各个领域内的专业人士,我轻松地介绍一下。马军被称为“环保斗士”,他目前所作的工作是信息技术,旨在让公众参与到环境信息的公开披露,以此来促进这个环保过程。我觉得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工作。今天《界面》恰好有一个采访朱小地院长的文章发表,其中有一句话很好,“建筑是生存在大地天空之间的创造,它应该具备这样的能力,我认为时空概念要用新的形式表达”,很好的切入了今天的话题。曹斐是广东人。作为艺术家,她一直关心人和城市的各种关系,关心现在,也关心未来,关心和人相关、和城市相关的各种问题。她的作品《霾》就是讨论雾霾和人的关系。

何力
现在喜欢说“后现代”,那么今天讨论之后,就进入到“后雾霾时代”。“后雾霾时代”可能指的纠结或内在矛盾,可能不单单是一个环境问题。我个人的体会是,当雾霾成为一个公共话题的时候,尤其是经过这一年逐渐强化以后,雾霾已经变成了一个“哈姆雷特”。一千个人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千个人心中就有一千种雾霾。雾霾问题既然有各式各样的说法,也就有各式各样的解释。我想引个借喻来简单阐述一下我对这个事件的认知。梁漱溟说,这个世界上的大事,也就是最重要的关系,其实只有三个:一个是人和自然的关系,一个是人和人的关系,一个是人自己和自己的关系。世间所有问题归结起来就是这三个关系。后来,我突然发现雾霾之所以发生,甚至愈演愈烈,跟这三个关系密切相关。
第一个“人和自然的关系”,不需赘述。当然即使这个关系也有其他的看法。我认识一个朋友是国家地理杂志的,同时亦是一位探险家。面对“人与自然”的问题,他就认为人类很容易自作多情,总是以为自己可以轻易地改变世界,但也许我们实际上处于一个历史性的周期。而从长周期来看,环境问题根本与人类环保不环保没有太大关系。在座的环保专家一会可以批评这种说法,但他也代表了一部分人的看法。
第二个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造成雾霾的原因之一。怎么说呢?我们想《气候公约》,它里面隐含了一个政治命题——即资本主义西方先发展、先排放。记得当时修三峡的时候,我和台湾记者及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几位老先生们在一起,在三峡上游的时候印象很深,我们说这个地方多么美丽、多需要保护,但是当地村民说凭什么我们要过这样条件落后的生活?放之环境问题是一样的。作为后发展的国家,凭什么我们人均碳排放不能高一些?美国人能开大SUV凭什么要求我们开QQ?现在人福利更重要还是子孙后代更重要?这个是平衡点。最好的环保是现在人把所有资源留给子孙后代,可哪个是正义的?公平的?人道的?这就有了争论。于是变成“人和人的关系”。你要发展我也要发展,所以还是要走工业化老路。第三“人和自己关系”的问题。这一点曹斐最有发言权,怎么去化解雾霾改变的人的内心世界。
雾霾从何而来?
马军:熟悉我的朋友都知道我主要做环境问题里的数据工作,可以说是非常枯燥乏味的事情。刚才何力提到三峡,实际上我与环境保护之间的第一个关联点恰好是从三峡开始的。1994年,我尚在《南华早报》工作,去三峡看文物,那时三峡尚有居民,沿河看到了很多漂亮的民居,除了民居之外,震撼我的是三峡上看到的一座接一座的荒山。车开到山顶,那么深的河谷中间,两岸都是秃山荒岭,这些原始森林都是在大跃进时期的短短一两年内全部被砍伐炼钢铁去了。
历来中国只有河患却鲜少有江患,就是因为长江有相当完善的上游林和中下游湖泊湿地的自我生态调节功能,这种功能一直维持到300年前,中下游遭到一些破坏,最后上游林在大跃进时期全部被砍掉了。人也是自然的一部分,我们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当中不可能不触碰到自然,可触碰到什么程度?人是否可以根本性的改变自然环境?“大跃进”那一段历史告诉我们,如果我们做得不对,真的有可能根本性地改变自然。50年代地球人口大概70亿人,现在马上90亿人了,人类到底应当怎么面对自然?这之间的关系确实需要重新思考。

马军
有些事情是说不清楚的,比如气候变化,但有一些问题是说得清的,而雾霾恰恰是可以“说得清”的问题。雾霾形成无非两点因素,第一是自然不利的气象条件,第二是我们人类生产生活当中不适当产生的大量污染的排放。雾霾不仅是一个代际公平的问题,它已经在代内形成了一个巨大问题。由前任卫生部长和现任环境科学院院长一起做的研究表示,按照最保守估计,每年因为雾霾(室外空气)而早亡的中国人在35到50万人之间,而国际测算很多甚至接近百万人,但就算是我们的官方数值,每年35到50万的早亡人数,难道是我们作为这一代人可以承受得了的吗?这还仅仅是雾霾这一个环境问题。需知很多污染引发的病变需要时间积累才会显现,与其说现在我们到底怎样面对它,毋宁说这个未来问题怎么处理。
气象因素,人为干预的能力非常小,但是污染排放方面的因素我们可以非常确定。在我们小小的现在所居住的一片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排放是多少呢?河北三亿吨煤,天津六七千万吨,北京大概四亿吨煤,还要再加上山东的数据。山东省烧四亿吨煤,全美国煤炭消耗量则是八亿,然而美国有那么大的国土面积,咱们却集中在这么狭小的范围内。那这个工业化、城市化的规模,达到了怎样不可想象的程度?中国和西方恰恰不同的一点在于中国80%的消耗是在工业生产当中,是生产方式导致的问题,而生产方式完全可以去改变它,因为它涉及到的都是严格的国家法律法规。指标和排放标准是非常清晰的。
人为干预形成的雾霾
何力:据说,2008年河北钢铁产能1亿1千万吨,政府说奥运会之后要砍掉,可是2014年还是2015年,钢铁产能反而变成了2亿1千万吨,非但没有砍下来反又翻了一倍?
马军:一亿吨太多了,治理后反而变成两亿,这是怎么来的?就是行政命令一刀切的后果,用“看得见的手”干预的结果。政策是每次低于若干产能的小企业就要一律关掉。那企业的反应是什么?自然是把舢板绑起来变成航空母舰。这样就有了产能巨大的河北钢铁工业集团。从前钢铁重镇是唐山,京津冀其他的地区基本都是搞农业副食。这个是有道理的,因为气象扩散条件的确非常不利于发展工业。为什么现在石家庄、保定、邢台、邯郸差不多一个月不能出霾?因为它们处于太行山的山前平原,霾一旦堆在那个地方,南风一起,就回旋不出去了。
工业化越来越严重, 我们已经消灭了城市与城市之间大片的缓冲地带,在气象条件最不利的条件中,环境容量最低的地区,如此密集和大规模的修建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的产业。中国作为一个世界工厂,至少应该是一个清洁生产的世界工厂,但是治理的手段如此武断。不是说谁的污染大才关闭谁,而是谁生产规模小才关闭谁,大国企、大央企不能触碰,最后导致我们长期建立不了一个建构在环境法治基础上的环保治理手段。
环境污染问题迟迟得不到解决,最核心不是缺乏技术和资金,核心是谁污染谁占便宜。这个动力可以解决,但是解决它需要全社会广泛参与,这个参与需要有环境信息的公开。基于这个想法,我们开始构建环保数据库,首先发布了水污染地图,2007年我们开始建造空气污染地图,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更多了解了空气污染对于健康的影响。
刚才我们谈道德,谈到信仰,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可如果法律不能得到有效的执行,那道德就变得十分苍白无力。如果大家都排队,你不排队,那鄙视的目光都会让你矮下头去。但是现在大家如果都破坏规则,道德力量会突然变得苍白。我说环境法治是非常重要,必须扭转长期以来形成的违法成本严重偏低、谁污染谁占便宜这样的现状。否则,市场力量将永远跟环保对着干。朱小地院长之前说今天来接受批评,但我们机构做10年环保,没有能够去真正的解决这些问题,反而雾霾问题更加严重,所以我们是愧疚的,但是我们也不失去希望!
城市化带来的困惑
朱小地:我认为我对雾霾的了解和做出的判断可能跟大家都是一样的,并不是这方面的专家,也没有做过这方面的研究,但是据我了解,建筑和城市建设这部分,在前期的工业加工制造过程当中,消耗能源大概占全国能源的15%,这是生产;那么在后期,因为这些建筑每年要保证供暖、能源供给,那部分能源要消耗大概24%。 中国的城市建筑所消耗的能源,基本上是煤炭、化石能源,这方面可能引起污染源头地追溯。我作为建筑师在中国,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几十年中,改了很多房子。就北京而言,原来的旧城即二环以内范围内,面积大概在62平方公里,由原来的平房往高层发展,这个建设量非常大的,造成中国用水泥量,用钢量成为全球第一。

朱小地
这个过程是急剧扩张的,而我注意到这其中有一个问题——我设计修建了很多住宅,并不是我们生产出的这么多房子都在充分地被使用,有一些房子甚至卖不出去,就连北京也有房屋空置率。二线三线城市房子卖不出去,甚至到了要卖房子都不行的地步。想卖房子不给你钱,给你一个票,然后凭这个票去兑换买新房,已经形成这么一个尴尬的局面了。雾霾北方几率出现很多,冬天会更高,冬天这么多房子,都要维持着一个基本的采暖需要,那整个的“采暖季”能源供给要消耗多少呢? 北京这几年做的还是不错的,“煤改气”,供暖全部都是天然气。天然气从哪来,还能供给多长时间?都不知道。北京很多烧煤的锅炉房全部改造成其他的了,但是以后如果没有天然气了怎么办,就很难说。
有时候我觉得生活在一个大城市里,感觉到很可怕。我们都是在搬运,分离农村和城市资源以及能源,以此来供给城市。其实我觉得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突然,我们水的污染其实早就有了。物质的东西进入到城市里有一定阻碍,农民会分离自己留着吃的菜和施了化肥的供给城市的菜,这个早就有了。现在空气污染了,没有办法城市和农村隔离我们大家都在“分享”雾霾。这就是现在的问题。
刚才说我们说“后雾霾时代”,雾霾已经有了,我们怎么办?我认为是社会现象。雾霾集中暴露了我们其实一直没有真正好好形成一个社会的合力,折射了我们在方便社会体系崩塌之后,中国社会怎么能够形成完整的社会整体、社会的共识,甚至公知的问题。我们在设计行业也一样,如果有一个好项目,或者说有一个费用更高项目,那我们也不会顾及,当然也做环评了,都做环评,可我们还是希望能够拿到这个项目的。现在雾霾无孔不入,房间内部其实指数也很高,我认为是一个反省,也包括我们行业如何能够应对这样一个局面,能够做什么。哪些是我们建筑师应该真正合理的,或者准确对待雾霾的这样一个对策呢?
现在行业内争论不休,比如说“全寿命周期”。“全寿命周期”有些专家提到增加建筑使用寿命,现在高耗能的、不合理的项目如果固定下来,这本身就是不合理。还有能源源头,到底是风能、太阳能、地热能?获得能源的同时,也制造了很多的能耗的问题,甚至也有不可持续的问题,这些怎么和我们建筑的能源使用相结合?以及包括我们现在能源管理问题,比如说现在很多房屋计量时,是没有考虑过能源计量的,比如暖气的采暖,导致房子改造好以后热得不得了,因为暖气没有办法的。市政暖气开的一样,消耗能源一样,结果恨不得脱光了在屋子里待着。这是因为没有形成一个社会整体的解决方案。我们也在努力,有时候也很困惑。
何力:这里牵扯到我们的整个这会建设实际上存在一个巨大的漏洞,或者说真空。胡兰成说“中国人信仰就是中国人历史观”,金观涛说从来没有一个文明像我们一样把家庭和国家对接得如此完美。中国人的价值观里没有社会这个单位,只有家与国。我们请曹斐来讲一讲,为什么你说雾霾很“魔”?
内心的雾霾
曹斐:我说雾霾“魔幻主义”,因为霾看不见,它阻挡很多视线。我住在16层,雾霾最严重的时候窗户外面一片白,晴天好的时候却可以看到中央电视台大楼,这个反差特别大。霾逼过来是一片白的光。我没有两位专家那么多数据,我是艺术家,感性又是一个母亲。孩子用“因为,所以”造的句是,“因为天气不好,所以我不能出去玩”。孩子问我,“妈妈,什么时候会有末日?”那我也是个很残酷的妈妈,说现在就是末日。如果我说末日快来了,小孩会很恐惧,如果我说现在就是末日,孩子觉得原来这就是末日呀!不可怕呀!所以很坦然。为什么我说现在是末日?因为全民动员都要戴口罩出门。口罩已经变成了一个必须,就像原始人慢慢有了衣服、女性慢慢有了胸罩……是不是以后口罩是人类的必需品了?我们不要说“后现代”,我们是在后末日!是末日后的状况下。这个武装是必须的。这其实是挺绝望的一种状态了!

曹斐
2011年冬天生我的女儿,2012年感受到很严重的霾,2013年我决定要拍一个关于“霾”的影片。实际上2013年我考虑过离开北京,因为我先生是新加坡人,哪里空气那么好,我就想为什么不走呢?关于《霾》我没有想过从环保角度,很多人问我是不是要解决环保问题、讨论环保问题,我觉得不是,还是要回到人本身,“人性”本身。刚才讨论的霾都是产能,而我想去到看不见的风景之外、还有体制背后看不见的东西、整个系统我们不可触碰的东西、普通人不可谈论的东西,这些反而比霾更难看得清、看得透。数据是看得见的可以被公布的东西,但是看不见的东西可多了。我们不谈环保,我们谈这个声音如何达到接收方。
我的影片谈的是,在后末日或者类似末日状态,人的这种压抑。这其中包括奥运后整个经济的停滞,人“找不北”的状态。《霾》是讲在中产阶级社区里不同人的状况和机遇,从不同阶层的人,清洁工、保安、直到中产阶级的住户,我用不同场景去表现他们的压抑,困惑和无助,最后里面住的人慢慢变成了行尸走肉的僵尸。当时也是受美剧《行尸走肉》影响,无名地走在森林里,突然的大波僵尸就过来了,非常魔幻。雾霾也是,有时候没有,有的时候整个森林,小树林,或者整个区域,50米外突然看不见了。这种东西从美学层面,人感知方面会有一种恐惧,恐怖!
莫大的城市,如果我看得见城市对面,就会有安全感。我觉得我生存在这个城市。可看到一片白的时候,万一发现什么问题,救援的人怎么知道我在哪里?它甚至形成了一种奇异的雾霾美学!有一天我看景,光刺进雾霾里非常美,像印象派的画,但其实是霾。所以从我个人角度,或者创作角度去触碰它。触碰不是说碰到霾,而是穿过霾我们能够触碰到什么。如果我们今天在末日状态下,刚才也说到一个长生命周期,那可能人类历史就是那么一段而已也有可能。我们今天即使再努力改变,可能也难逃像恐龙一样的必然灭绝。也许人类就是整个长生命周期里的一个点,就像看纪录片看到小蚂蚁建了巨大的巢,但是吃空了,依然会塌。可能人类生存就需要制造,就会面临危机,动物界也一样,也有灭绝的可能,也会在生命长周期慢慢完成自己的一部分。
马军:每个人最柔软部分就是在这里,我和我的儿子所经历最多的也是最激烈的争论,甚至是争吵,都是在因为周末我不让他出去骑车。我比他更早了解霾的危害,但是要让一个11、12岁的孩子周末不许出去玩又很痛心,我跟他这种争吵特别激烈,以至于在我车上按了一个自行车架子,带上他去坝上找蓝天。当时一路霾,到了坝上一下天蓝了,我们共同反映了就像鱼在极度缺氧的水里,突然把头伸出来那一下,就是大口吸这个,真的是吸进去了。
面对雾霾的“有所为”
马军:很多人就常常问,就疑问这个数据。在2013年以前,中国80%的城市被认为空气质量达标的,2013年公布数据,当年是80%以上不能达标,现在是78%不能达标。我们看空气质量和大使馆得出的不一样,不是数据不一样,是标准不一样,主要是美国的标准比较严格。同样是60,我们这里是“良”,他们那里是污染。总体是数据比以前靠谱了,因为一切自动状态,自动监测、传输和发布,所以数据有了很大提升。
现在讲我要找回蓝天,一蹴而肯定是非常困难的,还是需要步骤。第一步要监测和发布,我们到底知道这是雾还是霾,这一点取得了巨大进展。第二点预警和应急,从去年年底环保部每一次霾一来,提前预知指挥30-40个城市同时预警,这个我们应该感到欣慰,不然就是在不自知中受害。我们一定要从PM2.5这个空气质量的公开,逐渐转化到对污染源信息的公开。必须要完成这个转变,必须要知道谁排放PM2.5。曾经中国学习所有制度,环评也是每一步都借鉴别人,从来没有超越别人,但是没有想到几个月之后,在2013年7月份环保部下发了管理办法,要求国控重点污染源在线监测数据从2014年1月1号开始向社会公布。我们可以看到每一个省从那年底建设平台,向社会公开信息,但是还是不好找,20-30个平台,网站上也不好找。因此我们开始做“蔚蓝地图”app,把所有污染源信息在上面集成,集成后不但可以获取信息,公众也可以通过微博和微信分享,微博可以@环保部的官方微博形成“微举报”。大的电厂、石化,都是国企央企,公众反复举报下他们开始转变了。我讲这些是希望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不是在这个雾霾的时候无所作为的,我们实际上还是能够做一些什么事情的。
朱小地:刚才您跟我讲,如果我们治理得当的话,短在五年远到10年可以解决雾霾,或至少可以有一个断崖式的改变,这个我相信。那么为什么大家处在焦虑状态?我觉得我们在信息化高速发达时代,我们每个人寿命,或者说我们对于生命理解其实在大大缩短了,我们每年都觉得时间很快就过去了。所以我这里面有一个矛盾——时间在加快。过去说城市的霾,跟世界没有关系,但是现在世界连在一起了,我们要不然选择离开世界,要不然必须选择尽快解决。五年到十年时间并不很长,可是童年变成青年,可能这种曾被雾霾笼罩的阴影会一辈子影响他。我觉得这一点是现在公众对这个雾霾,或者面对污染显得焦虑的根源。甚至有可能公众态度会变的冷漠,谁知道什么时候能治理好?国家、自然、社会、个人没有现在形成一个共同的整体,我觉得这是我认为核心问题所在。我们是否可以真正的等待?雾霾一定可以治理好,但我们能不能拿生命中有效的时间可雾霾的治理去对立?我这一点是有矛盾的。

离不开的城市与回不去的家乡
何力:现在有一种不确定性——缺乏时间表和路线图。
马军:这就说到了环境经济学理论:搭便车,和外部性。“搭便车”就是说这件事确实改善了所有人都受益,但第一个冲到前面去做的代价不小,所以谁都不愿意冲到前面去弄这个事。
朱小地:这背后实际上是缺乏“社会乃公众治理的社会”这一概念,而是把所有的事情都推给政府处理。在国外开车窗丢垃圾别人会出来组织,因为这是他们自己生活的社会,公民社会治理结构是大家共同来关心的。我们现在变成了完全由政府结局,大家对公共问题越来越漠不关心,国人是这样的一种悲剧。孔子时期是讲究理智的,这种“君为臣纲,父为子纲”的关系逐渐衍变成了上下级关系,最后的结果就是只要没有被抓住就忘乎所以、什么都敢做了。今天我们在座的人还是处在有话语权、有影响力的状态,还有选择选。
马军:我们还是有话语权而且有选择权,但很多人面对着“离不开的城市,回不去家乡”。无法离开城市讨生活,家乡也不再是原来的家乡。没有雾霾,还有水污染、土地污染,移民的话也没有条件。对于他们来讲,悲剧性更加强!我们有选择,做出怎样的选择都有它的道理,社会公平公正是不是有一部分应该推动这些问题的解决?
当然刚才说“外部性”,它涉及到一个“公地悲剧”——公共牧场谁多放牧谁占便宜,最后过牧草场毁了。怎么解决?解决办法就是要产权明晰,但是空气切分不了。谁也无法明悉分割空气的归属和产权。
朱小地:那雾霾岂不是中国唯一的一件公平的事情。它没有特权。

集体行动的必要性
曹斐:你做NGO有没有受到政府压力?公布数据可能是双刃剑,出白名单可以,如果出黑名单这个数值怎么平衡?怎么在夹缝生存?
马军:环保组织在中国的确比较少。环保涉及到的大多是产权无法明晰的问题,这就需要依靠集体行动的力量去改善,而集体行动确实有困境。其实在国际上,往往也是污染的灾难严重到了某种程度,它才能激发出真正的集体行动。要知道环保组织在过去的二十几年间得到的资金相比于救灾、教育、扶贫等是很少的,只有2%-3%左右,现在在阿拉善基金会、阿里巴巴基金会、爱幼基金会的支持下,逐渐多了起来。那为什么环保组织依然有持续的空间?因为问题就摆在眼前,而且它是相对比较公平的。环境的问题大家都是受害者,都能强烈感觉到。如果在雾霾这么严重的时候还不能激发中国人采取集体行动的话,那么我想作为一个民族,我们就真是“德不配位”。
西方六十年代一些局部区域搞出很严重的水污染和空气污染。1970年时两千万西方公众走上街头,于是有了第一次“世界地球日”,继而有了环保的相应法律。最开始在西方环保执法也是执行不下去的,环保是拖后腿的,但因为司法系统是独立的,公民和NGO都到法院去起诉,逼迫法律采取行动。这其中,信息公开就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样一次又一次,从告污染企业、到把不作为环保局的局长、甚至联邦环保局局长都告上法庭,一次又一次迫使法律建立起自己的尊严,让人们知道守法是必须的。于是,我们看到70年代,80年代,90年代环境污染断崖式的迅速改善,空气污染,水污染都迅速改善。
我们难在什么地方?法院跟环保局一样,受制于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需要GDP,GDP增长需要这些企业,投资者的经济利益在里面,地方执政者的政绩也在里面,所有一切的一切都在此基础上。法院不受理,接受不审,审了不判,判了不执行,我们复制了西方所有有效的法律法规,但是三十多年没有得到有效的执行。我们就在这中间把自己给害了。信息公开对我们的意义在于,虽然法院不受理,但全球第三波环境管理浪潮正是基于信息公开来的。环境管理也许能一下子进入信息时代。我们现在讲“让每一根烟囱都公开”,实际上这是《环保法》和《大气法》这两则法令若付诸实施后所要求的,但是目前只有北京要求企业去公开数据。河北企业里,国控的有一些公开,但很多城市应该公开的都没有公开。山西国控几个月不公开了,天津也是。大家最近很关注的临汾二氧化硫严重污染,自从去年9月份开始严重超标,再也不发布任何数据了。这些事实能否成为我们集体行动的起点?我是期待的。
何力:总的来讲,业主维权方面和环境方面容忍度还是高一点。

治霾需要多少钱?
朱小地:就是如果治理好这个雾霾,一共要投多少钱?我们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综合今后几年发展状况,能不能支撑把这个事情做好?
马军:最新的一点进展是环境税,国家已经批了。原来收排污费,现在平移到收环境税,将来希望能够收得更多一些。从环境经济学来讲,收税确实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只要收的足够到位,让违法成本高于守法成本,但是在中国有刚才说到的地方保护,以及收上来的税怎么用,这都还存在一些让人疑问的地方。
《大气污染行动计划》预算差不多五年1.5万亿,《水污染行动计划》,五年2万亿,如果治理都用财政来切入的话,这个钱不得了。北京一地治霾列的就7600万亿。实际上这是机制上的问题,应该用看不见的手去调节,而不是用看得见的手去干预,只有从源头的机制调整,改变谁污染谁占便宜的机制,让市场发挥配置资源。去年有超过一千家以上的污染企业来我们这边,为什么呢?我们有一个“绿色供应链”的项目,很多国际时尚的品牌都在使用我们的数据去管理供应商,像优衣库、H&M、GUESS、玛莎百货……把压力推给品牌,让他们承诺签任何一单的时候要首先确认它没有污染问题。这样成功让一家很大的纺织厂治理了它每年1200万吨的污染废水。这个钱就不来自国家,来自工厂自己。

香港的环保新规
邵忠:从2017年开始,香港所有上市公司的年报新增了新的规定。第一个是企业的社会责任,企业的董事长都需身兼环保及社会责任委员会的一员,作为披露。第二点是必须披露该企业在环保方面做了哪些工作。这已经成为一个业绩公告里最重要的一环。这一项新增,是由香港联交所和证监会共同规定的。现在的企业不仅仅是一个优秀的商业行为,更有它所需肩负的社会责任,这项规定让考核一个优秀企业的标准发生了变化。
马军:我们做信息公开,实际上是一种“绿色选择”,数据和信息呈现在手机上,让每个人看到它,目的不是主导每个人怎么生活,而是我相信人类的理性,以及最重要的——回归理性。
这个世界会好吗?
何力:今天很感谢大家。最后我想起再借梁漱溟结束今天的夜话。梁漱溟的父亲大学者梁济在跳下积水潭的三天之前问他儿子:这个世界会好吗?二十五岁的梁漱溟当时还很年轻,他说,会好吧!但是梁济本身没有那么乐观的。贵为像梁济这样的精英知识分子,他也说过,“如果人民日子好起来,伦常是重要的”,这个意思是道理最重要,但他也说,“如果人民日子能好起来,伦常也可以变通嘛”,证明精英在九十九年前也是实用主义的。所以有时候“这个世界会好吗?”这个问题,它还真的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就到这吧,谢谢!
END













